《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》是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中心所出版的海洋史專著,旨在討論在尚未有蒸氣動力、僅能倚賴季風來橫越海洋的近代亞洲各國,如何透過各自不同的媒介與管道,一方面吸收外界資訊、二方面互相交流的過程。一月份的書評再次請到《從漢城到燕京──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》一書的作者吳政緯執筆,以其長期鑽研中、日、韓近代交流的學術背景,向讀者介紹此中研院的大部頭學術著作。
文/吳政緯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)
這像是充滿寓意的第一幕,而最先抵達長崎的是精通醫術的幼弟朱來章,關於他來日的緣由,必須追溯享保三年,西元1718年。這一年,幕府將軍德川吉宗(1684-1751)命令停泊長崎港灣的清朝商船,下次順風渡海,務必帶來一位良醫。
船頭李勝先、吳克修先後響應,他們分別載來蘇州的醫生吳載南,以及福建汀州的朱來章。朱來章表現極佳,醫術過人,因此幕府頒給他的外甥朱允光一枚臨時的寧波牌,以便他來日貿易,時在1723年,享保八年。
不過享保九年(1724),朱允光並未持著令牌渡海,而是在享保十年(1725),一口氣來了五位朱家人,他們分別是長兄朱佩章、次兄朱子章、幼弟朱來章,以及佩章之子朱允傳,還有身分不詳的朱雙玉。
朱佩章,本名綬,佩章是他的表字。他的舅舅李之鳳是遊走廣東一帶的商販,佩章耳濡目染,從小走遍大江南北,見識淵博。幕府沒有放過這麼一位「中國通」,派遣兩位日本儒者荻生觀(1669-1754)、深見有鄰(1691-1773)趕赴長崎,請教各種中國事情。過程中由懂得漢文的唐通事彭城藤治右衛門翻譯,荻生等人提出約數百條問題,再由朱佩章回答;這就是《清朝探事》、《仕置方問答書》的由來,一份份生於日本的中國觀察。
你會怎麼評價雍正皇帝(1678-1735)?這是在清代文獻不易尋獲「異見」的設問。《清朝探事》、《仕置方問答書》與朱佩章的自述《偶記》,為我們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,探訪十八世紀中國底層知識人的世界。根據此類材料,朱佩章眼中的康熙皇帝(1654-1722)「仁厚溫恭」,在位數十年間天下靜謐。雍正帝方面,儘管朱佩章承認今上即位之時「臣民之心未穩」,但雍正帝很快祭出雷霆手段,誅除阿其那(允禩)、塞思黑(允禟)等人,又整頓吏治,可說是「天下太平」。
朱佩章不僅能整體地論述國情,同時熟悉清朝的中央官僚制度、官員的配額與職掌,甚至能清楚辨別親王頭戴「七箇眼孔雀翎」,郡王則是「五箇」,堪稱瞭若指掌。至於各邊防要地,乃至三藩之亂後的駐防情形,也能一一陳述。朱佩章不是科舉出身,沒有功名,那怕他只是走跳江湖的商販,準確的見識仍叫人嘆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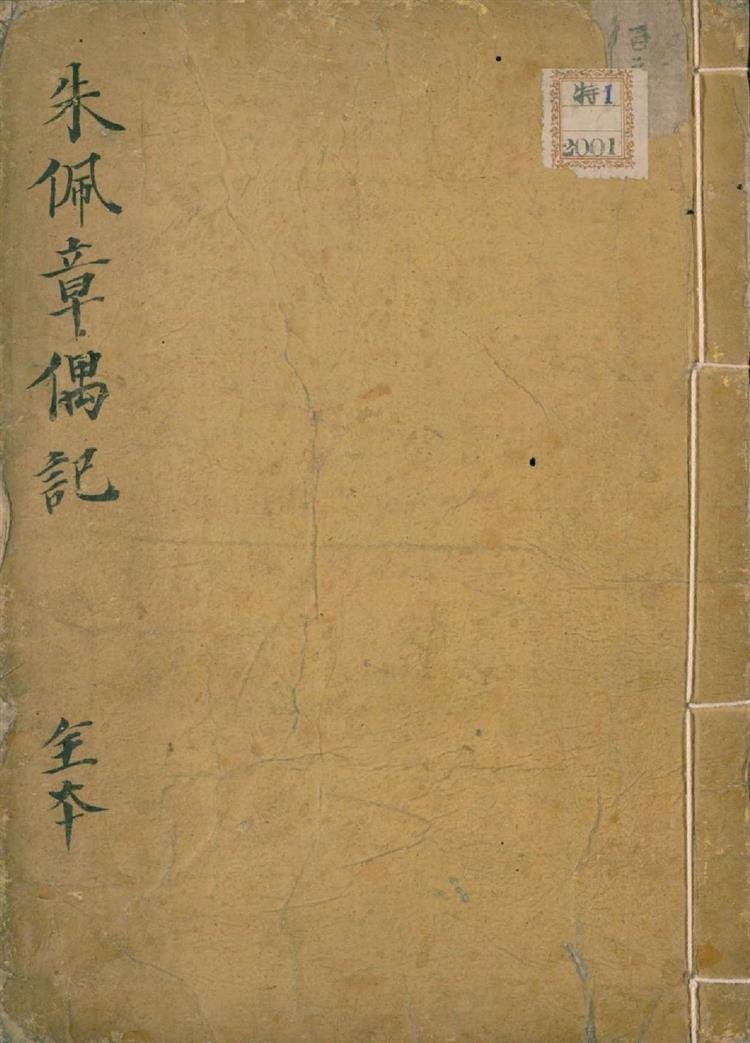 朱佩章的自述《偶記》,現存日本國會圖書館,請求記號「特1-2001」。
朱佩章的自述《偶記》,現存日本國會圖書館,請求記號「特1-2001」。
儘管時隔二百九十四年,這場在長崎進行的中日問答之所以重要,關鍵是背後交錯複雜的國際關係,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網絡。我們必須探究這場對話如何「可能」,才能在星羅棋布的聯繫中,確認朱佩章的話語從何而來,又將走向何方。
先說幕府賞給朱允光的信牌。在傳統的認知中,外國與中國聯繫必須倚靠「朝貢冊封體系」,加入者方能「貿易」。如眾所知,日本並未向大清國「朝貢」,但這無法抹除中日之間「非官方」交往的事實,否則朱來章無法渡日商貿,朱佩章與日本儒者的對話也將不復存在。
中日民間自由交易的現狀,在1715年迎來劇變。日本正德五年(1715),長崎官員為防止貴金屬持續出超,頒布「正德新例」,渡日華商必須從原本的八十艘降為三十艘,唯領有長崎官方發行的「信牌」,船隻才能入港貿易。[1]因此贈與朱允光臨時的寧波牌,不啻一種恩賞的特權,格外開恩,允你來貿;必須理解這一層,才能體會這份謝禮的重量。
其次是荻生、深見背後的主角德川吉宗。吉宗對清朝抱有極大的興趣,想方設法透過來日商船,進口中國出版物。說他對漢籍感興趣,不如說是藉此掌握清代中國的實況,於是各種詔令、奏議、政書、地方志,成為他訪求的藏品。荻生、深見此類通曉漢字、供職幕府的知識人便是整理、研讀這些舶來品的學者。[2]

日本幕府將軍德川吉宗像,德川紀念財團藏品。
早在朱佩章渡日前,遠在北京千里之外的江戶已有一個精讀《大明律》、《大清會典》的讀書會,成員之一的深見甚至著手翻譯《大清會典》,而紙頁上那些難解的文字,便隨著他拜見朱佩章,一一獲得解答。
晚近三十年,歷史學家益發關心跨越海洋的各種線索與聯繫。根據大阪大學桃木至朗的定義,海洋史不只是航海、貿易、海賊與海上人群的論題,還應包含海洋與陸地的交流與角力,也就是海洋與陸地的相互作用。[3]以日本學界的「海域亞洲史」(海域アジア史)為例,東京大學的村井章介提倡研究「跨國境的人、物、情報」(国境をまたぐ人・物・情報),過去為大陸中心史觀忽略的港市、海商,或是充滿刻板印象的禪僧、倭寇,均走出國別史的框架,呈現更多元的面孔。[4]
重訪外交使臣的歷程,以及追索漢籍、地圖、藥物的通路,史家將眼光放得更遠。這自然不全是為了研究「外國史」,而是冀望在更大的結構中尋找自己的身影。散落德川將軍身旁的地方志,乃至典章政書,期間透露的每一種制度與規範,都將成為日本統治者掌握大清國情的法門。
來往於漢城、江戶的朝鮮通信使,名義上旨在恭賀幕府將軍襲職,實際上歸國後總有一封上呈清朝官方的「日本國情報告書」。朱佩章留下的文字固然有趣,但沒有釐清背後龐大無垠的有機聯繫,便無法在適切的脈絡中掌握每一次文化交流的意義。那些在「域外」產生意義的事件,與其伴隨而生的「結構」同等重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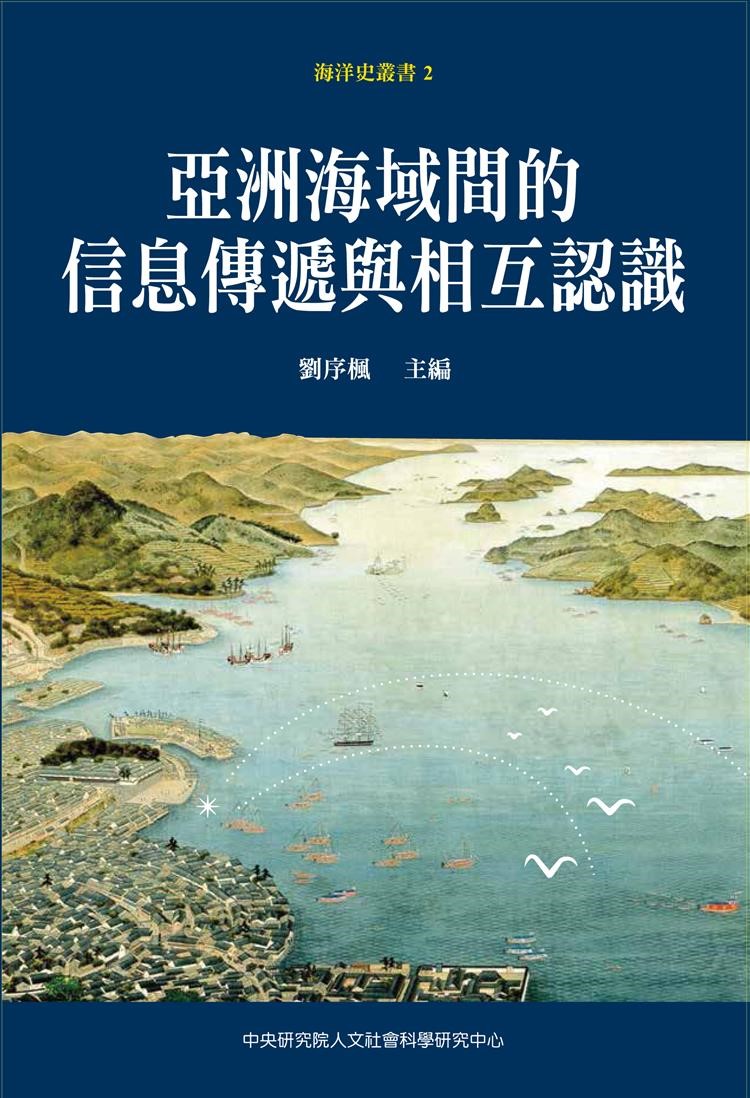
《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》書影。
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,「鎖國」像是常識,片板不得下海與被封鎖的日本列嶼充斥耳際。學院裡頭的專家早已離開這個論述很遠,他們陸續發現一幅「開放」的地圖「Mr. Selden’s Map」、靜靜躺在長崎的商業文書,以及朱佩章與荻生、深見的對談。一如書名《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》,當代學者已然衝過鎖國的桎梏,在遙遠的彼岸思索未來的歷史應該是甚麼樣子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[1] 羽田正編,小島毅兼修,張雅婷譯,《從海洋看歷史》(新北:廣場出版,2017),頁197-199。
[2] 川勝守,〈徳川吉宗御用漢籍の研究──近世日本の明清史研究序説〉,《九州文化史研究所紀要》,第32号(福岡,1987),頁293-383。
[3] 桃木至朗,《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》(東京:岩波書店,2008),頁1。
[4] 村井章介,《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》(東京:校倉書房,1988)。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│立即訂購│
國家書店→《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》
五南書店→無
a